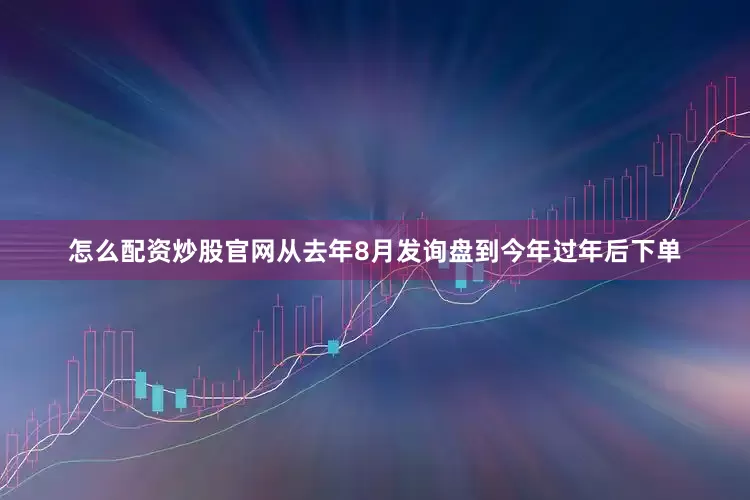“家”与“国”二字,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分量最重的两个字。孟子曾言“天下之本在国,国之本在家”,顾宪成则疾呼曰“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,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”。每当战乱之际,总有一批又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挺身而出,霍去病写下了“匈奴未灭,何以家为”的千古名句,《黄氏族谱》则将“皮之不存,毛将焉附?覆巢之下,岂有完卵?国之不存,何以为家?卫国御敌乃吾族之责也”的至理名言作为家族子弟教育与继承的家训。
壮哉斯言!正如一通矗立在长治市襄垣县的《殉国烈士纪念碑》所铭刻的:“华夏立国五千余年,其所以雄峙东亚,辉耀瀛寰者,自有其立国之精神在。顾亭林有言:‘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。’抗战诸烈士光荣殉国,从容就义,可见华夏立国精神赖此民族伟大气节也。”没有国,哪有家?正是因为有了丰碑所铭刻的烈士们的“光荣殉国,从容就义”,才维系了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与血脉。面对敌人最为疯狂之扫荡,山西广大的敌后根据地在最艰难之时,“抗日干部几不能存,日必徒居数村,夜必露宿山坡、窑洞。风寒暑热,雨露风霜,在所不避;枪林弹雨,牺牲流血,亦所不惜。敌虽凶顽,总战不胜人民的力量”(左权县《创建烈士祠碑记》)。
道家大家葛洪曾言“烈士之爱国也如家”,在抗战之际,舍“小家”而为“大家”,为国就义者比比皆是。襄垣县有一通《殉国烈士碑》记载了诸多烈士的故事,他们多是农民出身,但其身上却铭刻了中国人浸入血脉基因之中的家国情怀。我们在此仅摘录一则:“米国珍同志,三二岁,本区郭庄人,农民出身。抗战后,受不了日寇及封建势力的压迫,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,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。该同志曾担任过区粮食助理员和抗日村长。一九四一年,曾被敌寇汉奸米维士几次威胁其屈服自首。该同志不但不动摇,反而更加坚决脱离家庭,到区工作。于米家坪战斗中光荣牺牲。”
展开剩余53%再如《烈士李桂林暨刘元龙二同志纪念碑》中的李桂林同志,牺牲时仅有二十八岁,他是“石匣村人。自幼家境贫寒,债台高筑。父以做豆腐为业。”“抗战后,一九三八年春参加共产党,任小组长、支委。继任本村青救秘书,领导群众对统治者斗争。一九三九年七月,敌占辽城后,任十区财粮助理员,常在敌游区工作。敌捕捉其家属,威胁其屈服,然桂林同志蓄意坚贞,将家中老幼搬出根据地居住,摆脱了敌人毒手。”后“于襄垣战斗中身先士卒,指挥全体战士与敌搏斗,不幸光荣牺牲”。无论是襄垣县所立碑刻中米国珍同志“坚决脱离家庭,到区工作”,还是左权县所立碑刻中记载的李桂林同志的“蓄意坚贞”,都体现了中国人一种极为朴素的“家”与“国”的情怀,米国珍、李桂林等同志非不爱家,反而正是因为对家的深沉之爱,所以才甘愿选择了牺牲个体之家庭而奉献国家,彰显了一种崇高的爱国精神。
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”,是杜甫在《春望》中的一句诗,形象地勾勒了战乱之际民众妻离子散、音书不通时期的忧国与念家的情怀。在抗战之际,在三晋大地上有很多青年义无反顾地走上前线,直至牺牲才有消息传回家乡。在黎城县董壁村就有这样的一通碑刻,记载了村庄两位青年王泮荣、胡四良的事迹,他们虽已逝去,但他们的事迹铭于碑刻,仿若家书一样,一直矗立在该村,被家乡的人民不断诵读。碑文撰写道,“自抗战以来,我村青年踊跃参军,前仆后继。在民国三十一年参军时,王泮荣同志争先入伍”,后“终因特务汉奸配合敌寇,光荣牺牲”。“胡四良同志在七七事变后曾任青抗先部长,又当选杀敌英雄后,又任武委会副主任,于本年七月参加胜利军,开赴磁县,与敌伪奋斗一昼夜中伏身亡”,他们“忠于国家民族而牺牲”,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儿女。
“寸寸山河寸寸金”,从吕梁山到太行山,无数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我们这片土地,正是因为他们的“家国情怀”,正是因为他们的“舍身为国”,才造就了我们今日之欣欣向荣的中国!哀思祭忠魂,正如《晋绥边区党政军民殉国烈士纪念碑》中所发出的感叹:“滔滔汾河水,巍巍吕梁山,诸烈士之英名,将如水之长,如山之永,万世流芳,永垂不朽!”
贾登红
发布于:山西省睿迎网-睿迎网官网-配资网官网最新信息-a股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